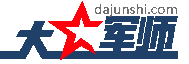●完颜文豪
今天回首往事,黄旭华也坦言,“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也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1950年代,春节期间,黄旭华出差到广东,经组织批准返回汕尾老家。
从零开始
2016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在远洋巡航40多年后退役,驻扎在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
然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仍在“服役”。
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以下简称“719所”)黄旭华的办公室里,除了几个装满书籍的柜子和靠在墙上的几堆材料外,最显眼的物件是两艘潜艇型号:较短的“体胖”是中国第一代“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稍长的“瘦身”是中国第一代“汉”级攻击核潜艇。
核潜艇诞生于 1954 年,也就是“鹦鹉螺号”首次试航的那一年。 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时有一句话形容核潜艇的续航能力:一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可以让潜艇行驶6万海里。
为打破美苏等国的核潜艇技术垄断,1958年,分管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研制导弹核潜艇。
经中央批准,组建了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后更名为09研究所)。黄旭华成为实验室的技术员。
他清楚地记得,这29个人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除了他已经嫁给了另外两三个人,“其他都是单身汉”。
随后,中央政府选派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加入实验室。在那个人才严重短缺的年代,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些大三学生也被选拔出来参与核潜艇的研制。
在1950年代后期的中国,没有人真正了解核潜艇,也没有参考资料。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嚣张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做不到!”
毛泽东回应:我们要自己研制核潜艇。
不久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让黄旭华这一代科研人员兴奋的话:“核潜艇将在一万年后建成!”

黄旭华知道自己和核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这辈子都要造核潜艇。”
采访过程中,黄旭华双手捧着核潜艇模型,像慈父在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孩子。
然而,那个时候,“孩子”的“样子”只存在于黄旭华的猜想中,“没有人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子,但普遍认为核潜艇大概是常规的中间有反应堆的动力潜艇。事实是根本不是这样的。”
“从物质到知识,用穷白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连基本的发展条件都没有,就开始做。”黄旭华回忆。
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一般都是在国外关于核潜艇的新闻报道中大海捞针,用算盘和计算尺来计算大量关于核潜艇的数据。
为了保证计算的准确性,开发人员分成两组或三组分别进行计算,如果出现不同的结果重新计算,直到得到一致的数据。
这让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加核潜艇深潜试验、现任719型总设计师的张金兰感到“难以想象”:“核潜艇的数据需要使用各种复杂高难度的计算公式和数字模型。”
幸运的是,有人从国外带回了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两个儿童模型玩具。玩具窗户打开后,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让黄旭华“很开心”。
他没想到,这两个玩具和他们根据零散的材料绘制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完全是凭想象。 “核潜艇就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p>
《不孝子》
“时刻严守国家秘密,不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做一辈子的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做好了剩下的工作“你的生活。即使你犯了错误,也只能留在单位清理。”在参与核潜艇研制时,领导向黄旭华提出了要求。
黄旭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普通科学家公开提出研究课题,稍有成功就急于发表,但你偷偷做项目,成就越多,埋得越深。你能忍受吗?”他的同学问他这个。
黄旭华肯定:“我能忍。我在大学的时候,经历过地下组织的严密纪律和组织训练和考验。相比之下,什么叫隐身?”
不过,今天回首往事,黄旭华也坦言,“身为无名英雄,也有难以忍受的痛苦。”说到母亲,黄旭华的声音顿时有些哽咽。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让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流下来。
1950年代,春节期间,黄旭华出差到广东,经组织批准返回汕尾老家。
它来来去去匆匆。母亲在告别三儿子时,留下了几句简单的希望的话:“你小时候离家出走,那时战乱,交通不便,你不能回家。”现在解放了,社会稳定了,交通恢复了,父母老了,希望你经常回家看看。”
黄旭华含着泪向妈妈承诺。他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三十年;再见面时,他的父亲和二哥都已经去世了。
他回忆说:“我父亲病重,我因为工作压力没有回去。父亲去世时,我没有回去参加葬礼。直到父亲去世,他才知道他的三儿子在北京。,我不知道地址,更别说我在做什么了。”
1956年,黄旭华与李诗颖结婚,次年大女儿黄燕妮出生。开始研制核潜艇后,几十年来,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李诗颖一个人打理。在女儿的心目中,“父亲的功劳有一半是母亲的”。
研制核潜艇的国家使命并没有给他太多时间陪伴家人。小女儿希望父亲带她去划船的愿望从小就没有实现。在黄燕妮的记忆中,父亲在家的最短时间还不到24小时。偶尔回家的路上,三个女儿跟爸爸开玩笑说:“爸爸,你又‘出差’了。”
在黄燕妮眼中,父亲“不轻易示爱,但很重视”。她记得很多年前,她妈妈在坐公交车的时候被人撞到,她受了重伤。医院发出危重病通知后,她父亲赶到医院,“哭得很伤心”。
1987年,上海《文汇报》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伟大而未知的人生》,描述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
黄旭华把文章寄给他在广东老家的母亲。文章只提到“黄总设计师”,没有名字。但文中“他的妻子李诗颖”三个字,却让妈妈坚信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她的三儿子。
没想到妈妈30年不回家,被哥哥姐姐们吐槽“不想回家,忘了养父母的不孝子”,所以才干起了大好事。国家。
多年后,黄旭华的姐姐告诉他,妈妈“一遍遍地看这篇文章,每次看都满脸泪水。”
母亲把儿孙叫到身边,说了一句感动了黄旭华几十年的话:“对于三哥(黄旭华),大家一定要了解和了解。”
亲情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彩色照片,他身穿黑色西装、裤子,打着领带,外搭白衬衫,左手叉腰站在台上,右手举起,目光炯炯有神。像少先队员一样敬礼。 2006年10月19日,黄旭华指挥合唱。

719年度文艺晚会结束,全体工作人员高唱《歌唱祖国》,总指挥黄旭华从82岁到87岁。
1940年代后期,在“国立交通大学”校园里,他喜欢打球、音乐和跳舞。
1945年,几经波折从桂林来到重庆的黄旭华被送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同时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第一名。他在海边长大,对海洋情有独钟,所以选择了当时被称为“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国立交通大学”。
1943年,我国著名船舶设计师、海洋教育家叶再富邀请辛宜新、王功衡、杨仁杰、杨洋等一大批英美高级造船人才加入“国立交通大学”,中国第一所。造船系的教学方法仿照麻省理工学院,使用相同的教材。
“我在交大上课的第一天,看到课本全是英文的,老师用英文在黑板上写字,考试还得用英文回答。那时,我的头很大。” 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老校友在建校120周年之际回忆进校印象。他说他只能加倍努力学习这些课程。年“终生受益”。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这位“爱喝粥吃红薯的穷学生”1947年在南京“护校”上访活动中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和《马赛曲》。
在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和腐败后,黄旭华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并提出“山上好地方,水田黄黄……你有上班吃饭,没人替你做。当时的“流行歌曲”《牛羊》被改编成《解放区,好地方……》,教学生唱歌。
黄旭华会吹口琴、二胡和扬琴。他说自己“不太会读五线谱”,但他五六岁的时候就熟悉了五线谱。到现在为止,他可以随意唱一首新歌的乐谱。
童年时期,音乐对黄旭华有一种离别的仪式感。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每次出门,妈妈都会组织孩子们唱几首歌。最后一首歌是每次离别的常规歌曲——基督教赞美诗《重逢》。
说起《重逢》,记忆停了下来,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场景,全家一起唱着歌。
广东海丰医生的父母,最初在教会医院学医,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生活中遇到疑难杂症,无能为力,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传承未来。他们的遗产是治愈和拯救生命。”
抗战爆发后,沿海省份学校停课。 1938年大年初四,14岁的黄旭华跟着大哥离开汕尾老家,听着妈妈的告别歌声。
当时,当日本飞机响起时,老师拿起小黑板,带领学生们进入甘蔗林继续讲课。夏天没有甘蔗林,黄旭华和同学们躲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树下上课。
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学校宣布解散,黄旭华不得不前往梅县、韶关、平石、桂林求学。
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每一次想家的时候,他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唱出那首熟悉又温暖的《重逢》。
进入桂林中学后,他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地方”。在日本飞机的一轮轰炸之后,这座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一片废墟。
流浪上学,不断躲避敌机轰炸的经历,让黄旭华在中学时就想到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为什么日军这么疯狂,想降落就降落,轰炸想轰炸的时候。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住在我的家乡,而是四处游荡。祖国那么大,我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学习?”
战争带给他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太弱了,“国家太弱了,就会被欺负宰割。我学医当然好,但我想学救国,我不想学医了,我想学航空和造船,以后我要造飞机保卫蓝天,造军舰抵御外来的海上侵略。”
黄旭华的家国情怀也影响了大女儿黄燕妮的一生。这位60岁的原719研究所女工程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从小就投身于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并跟随父亲的人生轨迹直至退休。
“潜水”完成
原719研究所研究室政委马干回忆喜欢唱歌的老同事黄旭华:“看来他是为工作而生的。‘文革’时期,‘战队白天批评他,晚上他还是去办公室上班。”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国防科研“缩短战线、排队任务、确保重点”的政策下,核潜艇研制任务被迫停止。 1962年,黄旭华任国防部第七研究所09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1965年,中央决定全面启动核潜艇研制工作。
1960年代,在“七级风一年两次,半年一次,冬天的寒风难忍”的葫芦岛,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征服核潜艇动力、线路、结构、水下声音、武器装备、通讯、生命保障等核心技术问题。
从核潜艇上发射导弹,首先要把导弹从水底推出,在空中升到一定高度,然后点燃。这种发射是摇摆不定的,位置会变,比陆地发射要困难得多。
造船系毕业的黄旭华知道,一艘4000多吨的船需要配备5万多件设备。如何准确测量各设备的重心,最终调整出理想的船重心,是一个前沿课题。
他用了一种比较原始的方法,派技术人员到设备厂去查每个设备的重量和重心。设备装上船时,在船体入口处放一个秤。所有带进来的东西都经过称重和登记。施工后取出的边角料和多余的管道电缆按比例扣除。
如此严谨的“装”态度结合原有的方法,最终发展出的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导弹时的稳定性完全满足发射条件的要求。
1970年,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战序列。迄今为止,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类型是“液滴型”。为了实现这种船体结构,美国采取了三个步骤:首先在常规潜艇上安装核动力装置,建造水滴式常规动力潜艇,然后将两者结合成核动力水滴型核潜艇。在黄旭华的带领下,中国“三步合一”,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研制出第一艘液滴式核潜艇。
当时国外权威文章提到,美国在核潜艇下安装了一个65吨的陀螺,发射导弹时利用陀螺高速旋转稳定船体。黄旭华坚持按照科学规律进行核潜艇试验,“为什么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结论,还得跟着美国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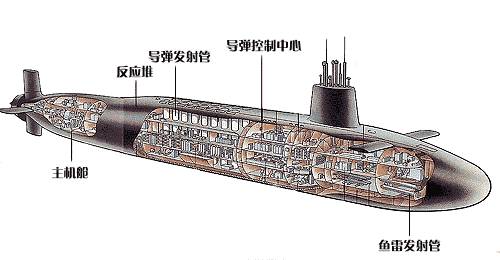
经过理论分析和测试,黄旭华大胆取消了这个设计,船体不用大陀螺也能保持稳定。
“我们核潜艇的设备、仪器和原材料都不是来自国外,船体的每一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黄旭华果断的说道。
1979年黄旭华任“09工程”副总设计师,1982年任总设计师。
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进行了第一次深潜试验。张金兰介绍,深潜试验是评估核潜艇在极端条件下的结构和出海通道系统的安全性,而核潜艇的深水试验是最具风险和挑战性的。
“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可以承受一吨多的水压和一百多米长的船体。任何不合格的钢板、焊缝问题或阀门关闭不充分都可能导致船失败。毁灭。”黄旭华讲述深潜实验的危险。
实验开始前,几名船员偷偷写信给家人,“万一他们不回来,家里会处理未竟的事”,这实际上是一封遗书。更多的人在宿舍里默默地哼着《血色风采》,“也许我说再见就再也回不来了……”
64岁的黄旭华当即决定一起潜水,给了船员们信心。随着100米、200米……距离核潜艇的连续命令,黄旭华神色平静,指挥稳重,但“内心很紧张。”
测试成功。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下船后即兴写下:六十六傻,智探龙宫;狂风暴雨,尽情享受吧!
“潜水”的心还在
1988年,在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将任务型接力棒交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 20多年来,他为年轻一代充当“啦啦队长”,“关键时刻支持他们”,还充当“场外教练”,“不是教练,只是帮助他们了解大型实验中何时出现问题。”
时至今日,黄旭华与核潜艇之间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这位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8点30分到办公室,整理好几十年工作积累的几堆1米多高的材料,希望留给年轻一代。
他不需要助手和保姆,经常自己拿起水壶打水。多年来,我一直过着不可动摇和规律的生活。我早上六点起床,六点三十分去太极拳和长拳,七点吃饭,然后上班。下午在家的时候,他喜欢看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以澄清过去的历史事件。
然而,93岁的他,身体每天只允许他工作一个上午,而且他常常觉得“年纪越大,时间越少”。
他从不觉得普通。有媒体称他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坚决反对。在他心目中,核电专家赵仁凯、彭世禄、导弹专家黄伟禄都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是全国数千万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
在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庆典上,黄旭华回忆说,719所成立之初,“一个订单,300名科技人员放弃了上海、上海等工作条件优越的城市。北京,又去了荒凉的葫芦岛。十几年过去了,他们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5年出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大二学生迟松恒站在黄旭华20米的地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撼。他听这位老校友讲“这些技术人员一生奉献自己的结论是‘今生属于祖国,今生属于核潜艇,今生无悔无悔我投身于核潜艇事业。'"
站在他面前的老人让池松衡在他21年的成长经历中第一次发现了“报国”、“献身国防事业”、“国家使命”的宏大理念,最真实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