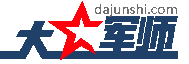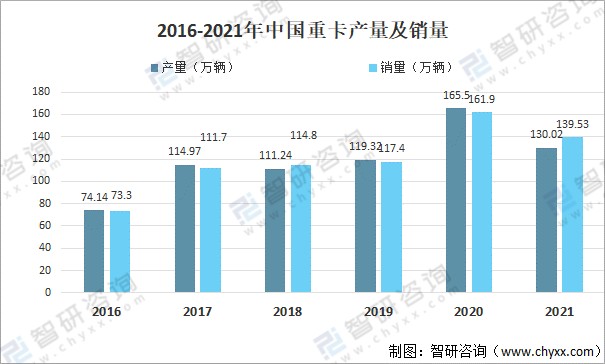就像种树人种了二十几年的树,终于接二连三地,长出了新芽,深处是浇不灭的热爱和渴望。
文 | 金钟
编辑 | 桑柳
银幕背面,心愿的开始
这是所有人期待的夜晚。几百人早早到场,等放映员上班。灯光熄灭,一片黑暗中,人人屏息等待。一束光打过来,胶片转动,幕布上出现了男人和女人,还有一些陌生玄妙的世界——电影开场了。
看着银幕上的人影,台下的小男孩对幕后的世界好奇:电影里的人为什么这么高?电影结束了,他们去了哪里?他想走到幕布后面看一看。
这个场景在演员张译身上一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十岁时,父母带他去看电影,他是绕到幕布后一探究竟的小男孩,那部电影是《红高粱》。第二次是他四十岁时,成了张艺谋电影《一秒钟》的男主角,一个追着电影放映、想要看一眼已逝女儿最后影像的劳改犯。
从观众变成演员,三十年的心愿成真。
张艺谋导演的最近两部电影《一秒钟》、《悬崖之上》,张译都是主演。他是最职业的演员之一。拍《一秒钟》,张艺谋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减肥。他就在20天减了20斤,瘦到了110斤,一顿面食没碰过。
后来拍《悬崖之上》,有一场被电击的戏,张艺谋提出可以用替身,不露脸的画面由替身完成。张译拒绝了——人接受电击的状态,如果没有真实的刺激,很难演,他就真的受了电击。还有一场戏,漫天大雪里他和沙溢互搏。道具组提供的是假刀,他提出要用真刀。那把真刀去了刃,最后插进了他嘴里。
张译杀青后,张艺谋拿着扩音器,当着剧组许多人说了一番话——张译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非常非常敬业。有这样好的演员,中国电影是大有希望的。
这两年,张译是影院观众最熟悉的面孔之一。从《八佰》《金刚川》到《一秒钟》《悬崖之上》,他成为中国第五个突破百亿票房大关的男演员。有人看完他演的《我和我的祖国》之后说,在那年国庆档的所有电影、50多位参演的知名演员里,他最忘不了的,就是没有露脸的张译,口罩之上的那双眼睛。
但张译在知乎上关注过的一个问题反而是,演员拍烂戏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这似乎才是大多数演员的真实遭遇,更深一些看,也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命题:当我们许下心愿的时候,我们许下的到底是什么?一个出生时没有拥有那么多的人,配不配做梦?一个身在污泥中的人,要经过多少努力,才能成为自己?
张译后来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并不是坏事,他拍过很多戏,做过群演和客串,是一个从戏壳子里爬出来的人。「如果说在一部戏里认真表演,那是你应当应分的事。但在每部戏里,都做到认真表演,才能是个好演员。」
而现在他获得的一切,都是从戏壳子里长出来的。就像种树人种了二十几年的树,终于接二连三地,长出了新芽,深处是浇不灭的热爱和渴望。
图源《一秒钟》剧照
击不垮的十年
前段时间,张译突然想看看自己最早演戏是什么样子,就把第一次演的电视剧找了出来。是1996年的片子,找出来一看,难受了,当时的演技,用他的话说,是崩塌。镜头前那个青年,脸还没长开,不会演戏,又紧张又怯场,从现在的视角看,似乎没有任何成为演员的可能。
在许下心愿要当演员之后的很多年,张译都是在这样一种近乎微茫的希望中度过的。
从很小开始,他就有一种少见的敏感。小时候读《红楼梦》,很多内容他都还不太懂,但读到结尾,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能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小时候,他住在作家萧红的故居隔壁,后来读了她的书,他在文章里写:我自旧的商市街转来,默立上中央大街的石头,闭目:你还冷吗?还饿吗?你我的朝向可曾一致?可曾穿过你的身体?
在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第一次被话剧击中——东北剧作家张明媛有一部戏,叫《一人头上一方天》。他看完,在台下哭得不能自已。觉得舞台如此神圣,可以撞击人的灵魂。他四处找话剧剧本看,有人建议他去北京,天天都能看话剧。
他后来的老师彭澎对《人物》回忆过当年他见到张译的样子,站没站样,站那儿八道弯那种……那么个瘦子,脖子又长,当时觉得这孩子形象不好。这是18岁那年,初到北京的张译。
受限于长相,他在北影和中戏的考试中双双落榜。面试时,中戏表演系的老师尴尬地问他:考不考虑去中文系或者导演系?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因为体检不达标,他甚至都没有见到主考官。最后是北京军区的战友话剧团,用自费生的名额,收留了他。
入了剧团,一呆就是十年。但这却是另一段沮丧之路的开始。在接受《人物》采访时他回忆过,当时自己没长开,在舞台上肢体都是僵硬的,没有协调感。说话也永远像在播音,像在朗诵。演什么戏都很紧张,不真实。常常被人说:张译,你演戏就是一个死。
没有选择了,他只能做会议记录员,写宣传稿。偶尔能跑跑龙套,他就想尽办法给自己加戏。比如演话剧,他演普通村民,他就用纱布把胳膊吊起来、拄拐棍、临场发挥踢另一个演员一脚,观众没注意到他,反倒是导演把他臭骂了一顿。
就在那时,一部改变他人生的话剧出现了,《爱尔纳·突击》,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原版话剧,由当时剧团里的笔杆子兰晓龙执笔。
在这部戏里,张译是活道具、群众演员、画外音、场记,以及角色袁朗B角。说是B角,但实际是永远上不了台的演员——就算袁朗A角的演员因故不能出演,团里都会去别处找演员,而不是让张译上台。
这个戏,排了整整六年。有许多个夜晚,当排练结束了,张译都会留到最后,假装锁门。等大家都走了,他就会回到舞台,在黑暗里,把整场戏再演一遍。
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些经历以后都会派上用场。二十五六岁了,他没有钱,每天吃六块钱的拌饭,开始谋新出路。比如写剧本,从枪手做到编剧。最辛苦的一次,用4个月写了18集剧本,最后资方撤资,一分钱也没拿到。
走投无路,四处找剧组跑龙套。到了《乔家大院》,演陈建斌的跟班儿。在剧组,导演胡玫问他,小张译,你几岁了?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你记着,男演员28岁再不出来,就洗洗睡吧。
他听了,心里一惊——那一年,他已经27岁了。
一封信之后的转折
也就是那一年,男演员的年龄警钟即将敲响的时刻,机会真的来了——导演康洪雷看到了《爱尔纳·突击》,决定把它改成电视剧《士兵突击》。
知道这个消息,张译连夜写了一封请战书。信里有一句话,我做梦都梦见过自己演许三多。这里面有动人的诚挚,也有酸楚。
在那之前,康洪雷已经和张译合作过电视剧《民工》。张译演男三号,出戏慢,没自信,但康洪雷赏识他,给他准备了超出正常演员3倍的磁带,让他慢慢拍。
他最终没有让张译演许三多,但给了他班长史今的角色。后来,《士兵突击》大火,走红之后的生活,张译在访谈节目中说起过,自己穿着大裤衩出门买鸡蛋,被人认出来,提着鸡蛋兜头就跑,结果跑得太急,鸡蛋在树上撞碎了,蛋液就顺着网兜往下滴。
图源《士兵突击》剧照
那之后,张译又继续参演了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拍了几部都市爱情剧,又开始和电影导演们合作,从贾樟柯、陈凯歌到张艺谋。
过去十多年,在暗处、在幕后,跑龙套、当配角的日子,反倒成了他最好的养料。他演那些在时代浪潮中的小人物,有无穷的乐趣。
比如《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孟烦了,一个臊眉耷眼、没那么有斗志、心里满是怀疑和不相信的人,苍凉地活到最后。在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里,他演乍富的煤老板张晋生,教恋人开汽车,车子撞在石碑上,心疼,又假装无所谓,抬脚踹了车的保险杠,结果保险杠直接掉下来。这是电影里最好的包袱之一,是张译即兴加的。
就算是不那么重要的角色,他也会留下光彩。在《我不是潘金莲》里,他演审判长贾聪明。镜头里,一群人围住上访户李雪莲,突然有一只手,紧紧拽住她的书包带——粗暴、强硬、青筋暴露。有熟悉他的朋友猜,戏这么多,一定是张译的手。发微信一问,果然没错。
2015年,张译凭借电影《亲爱的》,拿到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男配角。上台后,他一口气感谢了17个人。后来他说,他想象很多遍,万一拿奖了,要不要就在台上只说一句谢谢——那样很酷。但那是他18岁起,立志做演员以来,人生第一次在表演上得到认可,他不想浪费那次机会。
一位曾被认为演戏就是个死的演员,熬了接近二十年,心愿终于得以完成。
图源《亲爱的》剧照
荣耀固然好,但快乐最难得
去年,张译很少见地上了一次访谈节目,他讲起,这些年很多综艺找到他,但他从没接过——在电影与电视剧之外,张译确实是演员里少见的隐形人。
这种对声名的隔膜,大概跟他在部队的十年经历有关。在剧团里,演出完有鲜花和掌声,有人找他签名,还会有一顿丰盛的饭,他往往会偷偷装一听可乐在包里。回剧团之后,继续是暴风骤雨般的批评,谁演得不好,要写检查,罚站,站军姿。
真正幸福的是什么时候呢?是这些事情全都过去之后,晚上哥儿几个趴在被窝里,不敢开手电,用被子蒙住了之后,闷闷地打开可乐,砰的一声,喝进去一口之后,打出一个长嗝……我最喜欢的是平淡的日子,我本身就有恐惧和抗拒热闹的场面。
所以每次听到其他人的夸奖,他总会觉得不真实。他最认同的评价,来自贾樟柯。在演了《山河故人》里的煤老板之后,贾樟柯用山西话点评他:张老板,能行——不是说太好了,太棒了,而是还可以,还ok。
在演戏之外,他已经建立起自己朴素快乐的生活——他爱猫,家里养着七只猫,在家里士兵突击老a剧照,猫有专门的卧室,与他的卧室相邻。他在墙上给它们掏了洞,有通道相连,他认为这是对猫的尊重。他在知乎的自我介绍是猫和观众的侍者。
拍戏时,他珍视镜头前的所有时刻,影像的东西要比我们活得长远,几百年、几千年以后它都能留存,那多值。但不拍戏的时候,他最珍视的,就是这一份简单的快乐,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自得其乐,要比人前无限风光更有意义。
这就是张译的美好生活士兵突击老a剧照,持续三十年的心愿成真了,背后是他漫长的付出,有改变,也有坚持。
不仅是张译,心愿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生最美好的期待,有的人的愿望是让山里的孩子多走出去一个,有的人的愿望是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还有一些微小但可爱的愿望,比如可以去游乐园,还有人的愿望是瘦十斤、收入再多点,或者是跑完五公里、通过考试……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些微小或者宏大的愿望在漫长持续的付出中走向自己理想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