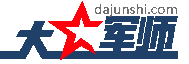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佳作《交响乐》——
文学书写战争的新视域
■朱向前
《交响乐》是一部饱含了深厚的民族精神,而又呼应了强烈的时代呐喊,回旋着激越的中国主旋律的宏大交响乐章,充分展现了王筠作为一个军旅作家的使命与担当。
王筠服役过的部队,曾是长津湖战役的主力部队,因此,将这段历史告诉世人,他一直视为使命。从那时至今,经过20多年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和10年的专业写作,他创作了包括《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在内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三部曲,共160万言,成为继魏巍之后,用多部长篇小说,全景式呈现抗美援朝战争雄奇史诗的作家。在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时候,确有回望那一段铁血和荣光历史的必要。如何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评价、总结那一场伟大的战争,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协作发展的前景,《交响乐》作出了有力的回答。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始终面对三个层面的问题:不断重新认识历史,努力还原历史,无限接近历史真相;反复深入开掘历史,仔细打捞历史细节,用心触摸历史肌理;投入激情激活历史,完成历史的文学转化,诗意地呈现历史。我们不妨以此三点观照一下70年来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及其在此背景下的《交响乐》。
大体而言,70年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期间。诗歌,如柯原的《一把炒面一把雪》、未央的《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了》;通讯,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中篇小说,如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风雪东线》《上甘岭》;长篇小说,如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等,掀起了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第一波高潮。但此阶段,总体是战时枪杆诗、战地通讯和小说的“急就章”。毋庸置疑,它们为抗美援朝精神和新中国形象的宣传、鼓舞和塑形的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但艺术成就也受到时代局限。
第二阶段,战争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巴金的小说《团圆》写于1961年,主要是一个父女团圆的故事,几乎没有正面的战场描写,跟《上甘岭》一样,都是通过电影的二度创作而产生了广泛巨大的影响。差不多与此同时开笔的,还有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完成于1978年。这部作品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开创了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先河,是当时朝鲜战争文学的集大成者。随后又有孟伟哉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中篇小说《一座雕像的诞生》等为代表的深耕细作,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英雄典型塑造,全景式画卷的展开,艺术表现手法的精致与完善。
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启了新时期书写抗美援朝的新篇章。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作品主要有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王树增的《朝鲜战争》、叶雨蒙的《汉江血》等纪实文学,创作者开始以纪实文学的方式逐渐还原历史。《交响乐》在这一个维度上继续推进,通过潜心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再实地、实物、实情、实景地描写。比如通过“脚蹬式”步枪的描写,就显示了中美双方武器装备不止一代的“代际差”。其实,王筠当年的长篇小说《长津湖》就是在长津湖战役60年后的一个大揭秘。60年后,美国以《最寒冷的冬天》、中国以《长津湖》这样的文学范式同时揭秘了这一场极度严寒条件下中美两军主力部队的生死对决,将这段无比残酷的历史展示在世人面前。王筠最新出版的《交响乐》再次涉及到诸多历史真实。面对历史,作者并没有刻意炒作和渲染,而是很自然地在叙述中完成了对历史的还原。既突出了我方装备老旧、保障落后,也表现了美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火力优势,和我们以巨大伤亡牺牲换来的胜利。如孟正平率领的穿插营,战至最后,600多人只剩下20余人。那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象征,意味着这冰冷数字后面的巨大代价和同样巨大的精神与意志力。它们是文学,也是历史。
打捞历史细节,触摸历史肌理。在《交响乐》中,小到我军各种武器的拼凑状况,从“脚蹬式”步枪到苏式“波波沙冲锋枪”,再到美式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和M1式卡宾枪,对二三十种轻重武器口径、性能的详细描写;大到对战争历史、地域、环境和双方战斗目标、战斗组织、战术特点以及给养补充等全方位的精细还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场知识链条。还有马老师与“喇叭刘”父子的打赌参军等情节,都新鲜、真实而富有时代感。至于以家乡的山川风貌甚至鲜花野草植入战场,就更带来了丰满鲜活的历史风貌。
诗意地呈现历史。《交响乐》首先是写活了一组人物:李八里、孟正平、张仁清、“大脚怪”鲍喜来、马永礼、王翠兰、“喇叭刘”父子等,栩栩如生,各有声口。写美军也有突破,不是简单地贴上美帝国主义的标签,而是首先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比如拉夫纳少将、库克中校、纽曼上尉、托马斯中士、小蒙特二等兵等都写出了一些性格特点,比以前很多作品中对美军的虚化、脸谱化有长足的进步。如纽曼的几次被俘,与吴了了的交往、接触、交流,甚至一定程度的认同乃至欣赏都比较自然,包括死在美机的扫射之下也水到渠成,而且寓意了战争的无情。比较而言,《交响乐》对我军人物的塑造就更丰富扎实,而且注意到从文化上做功课。李八里这个人物孝顺,早年就因父亲生病脱队跑过一次,现场又因母亲而只身出面谈判,体现的是孝文化,也铺垫了人物性格和行动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个人,他讲究孝道;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更讲究小孝服从于大忠,在国家与民族利益前面,置生死于度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孝道的应有之义。马永礼更是体现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三句话不离仁义礼智信,慢言细语,温文儒雅,是典型的书生。“喇叭刘”父子的响器文化与小蒙特二等兵的萨克斯共鸣、合奏,象征着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满怀理想主义,表达了对爱的呼唤。
在此基础上,小说还赋予每个人物以人性与真情,用人性与生命的交响呼唤友爱与和平。不光注重写我方的战友情、父子情、家乡情、爱情、家国情,甚至也注意到了敌方的人之常情。托马斯对小蒙特虽然恶语相向,却并不妨碍生死关头的以命相救,也是一种真实的战友之情。同时,小说还通过一幕幕惨烈的场景,既让人对于作品人物的英雄气概由衷敬佩,也让人为那些英雄或普通人的命运扼腕叹息。可以说,作品既是对英雄的赞颂,也是对战争的控诉,这个庞大繁杂的交响乐主题,就是对和平的祈祷。
就此而言,王筠实现了自己的追求:通过书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伟大的战争,既写出了一个民族站立起来的灵魂,又传达了一个爱的主题——沟通人性之爱、人类之爱,表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二元对立的阶级叙事与革命英雄主义赞歌以外,开辟了从文化冲突视角诠释和平价值与人性升华的新鲜视域。这种拓展使得《长津湖》与《交响乐》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学向度,显示出与以往同类作品的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