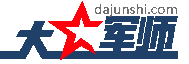记者李心玲、谢翔
40年前的6月17日,一架小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降落伞。当降落伞降落到离地3000米左右的高度时,降落伞包爆炸了,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爆炸声在空中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中国拥有氢弹的消息震惊世界!因为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综合国力,只用了两年八个月。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四十年后,几位专家回首往事,讲述了一些刻在他们心中的历史。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明确指出:“有原子弹,氢弹一定要快”。然而,氢弹的发展是理论和制造技术。比原子弹还要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对氢弹技术严格保密。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英祥看到,美国有记者曾在科普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及氢弹问题。结果,记者被美国当局审查,认为他泄露了氢弹的信息。秘密。事实上,文章中引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公开出版物。
一位专家曾说过,不可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是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氢弹的研制完全是自力更生,从零开始摸索。
p>
从哪里开始?当时,研究人员只知道氢弹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弹通过原子裂变反应产生能量,而氢弹通过原子聚变反应产生能量。众所周知,氢弹的当量是原子弹的数十倍或数百倍。至于如何制造氢弹,没有人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
李英祥回忆说,年轻的科研团队迅速投入工作,先后设计了几十个方案。一个接一个的方案经常被提出然后被拒绝。毫无疑问”的情况。技术和精神上的探索非常艰苦。当时被誉为“中国第一国内专家”的于敏院士,从30多岁开始就一直“隐姓埋名”,参与研究氢弹的原理。计算复杂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1960年代初期,上海只有一台计算机每秒可以执行10,000次操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当时紧锣密鼓进行的原子弹试验上,余敏和他的同事们经常拿着一个计算尺来计算白天和黑夜。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参数,觉得很重要,但怀疑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于敏想了好几天。一天晚上,他一觉睡到半夜,突然从梦中惊醒,拉住妻子的手,大声喊道:“是,是,我清楚,我清楚!”让睡着的女士不知所措。经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于敏突然有了灵感,实现了梦想的突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其中艰辛是脑力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叠加。李英祥说设计美国氢弹的人是谁,1965年,氢弹研制计划已经取得进展,几十名研究人员不得不从北京赶往上海,在电脑上进行计算。当时条件有限,上海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带着自己的被褥出门。
当时电脑用计算磁带打印出来的结果,很麻烦,而且计算磁带都是堆起来装在麻袋里的。科学家们花费大量时间仔细查看每条纸条,因为每一个计算机的眼睛都无法被打破,这可能会导致正确数据的丢失。
在这样的条件下,从1965年9月开始,经过100天的计算,在能源的一个关键点上取得了突破。在这个问题突破之后,整个氢弹的研制似乎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进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家贤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到上海,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都很开心。
统计显示:邓家贤,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钊,32岁;欧阳宇,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英雄,加入核工业时只有30岁。早些年。在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年轻人占68%,26-35岁占25.5%,两者之和超过90%。
“金沙滩”上的青春奋斗
一位法国专家曾问钱三强:为什么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前期准备材料和理论”。
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青海金银滩草原已经开始建设221基地。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家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在221基地研制组装,运往西部试验场。
今年70岁高龄的王景恒,曾任221厂厂长。他见证了一群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年轻人的奉献和奋斗。
1960年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王景衡就接到了“前进”的通知。前面在哪里?在西宁。单位叫什么?青海省第五建设工程公司。因为是国防,王景恒知道是个掩码。
1961年1月,王景恒和四个同学从北京出发前往兰州。当时,兰州至西宁的动车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只能乘坐以闷油罐车为主的“混合列车”。晚上,四个人挤在闷油罐车的角落里。西北的冬夜寒冷刺骨,三个人只穿了一件小棉袄。一个同学脱下了他唯一的一件棉衣,四人围坐一圈盖住,但他的手脚还是冻得麻木。运行了近10个小时,火车终于到达了西宁站,但从西宁到基地仍然没有交通工具。中国新年快到了。四个人在西宁呆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一辆卡车把生活用品送到基地。他们穿上当时给的四件:狗皮帽、棉大衣、大脚趾鞋、毛毡,然后坐在卡车的泡菜罐子上,被咬下转移到基地冷风。
“头顶蓝天,脚踩草原,我克服饥饿拯救了团队。”王景珩说,用这几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情况非常贴切。那个时候,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了。这支队伍能不能熬过生存考验,就关系到原子弹能否如期研制出来的问题,否则就半途而废了。因此,第一年,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厂。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小米面,一个月两元油,几乎没有副食,只能吃白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 “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锻炼,我得到了锻炼,站稳了脚跟。”王景恒说,当时虽然困难,但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乐观乐观,觉得我们的事业大有可为,只要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
当时保密要求非常严格,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矿区公所。高原除了缺氧,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得很黑,却不能告诉家人自己的事业。有同志回家,孩子问:“爸,你在矿区工作,你挖煤吗?”爸爸只能回答:“是的。”
在“矿区”的科研团队中,有一群科学家,王干昌、郭永怀、彭焕武、朱光亚、陈能宽……王干昌在基地呆了十多年.
1963年,王景恒被分配到221厂核材料车间,一直从事原子弹和氢弹原材料的最后精整、成型和组装工作。
“科技民主”促进发展速度
“技术民主”是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英祥说:“有些院士谈起这个还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其中有王干昌这样的老一辈,还有朱光亚、邓家贤等年轻一代。这些专家他们都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没有人看到或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如何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他们的心也没有底。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英祥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讨论设计美国氢弹的人是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讨论中,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想象力,擦出许多科学思想的火花,其中一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是新的设计思想,包括氢弹的原理。突破。
“这种全技术的民主,让人感觉很舒服,凝聚了大家的智慧,调动了大家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王景恒说。
李英祥说,40年后回顾氢弹的成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我们的领导和科研人员应该像当年一样有信心。本报,北京,6月16日